殷墟传统之外:三星堆早期发掘与早期中国考古学
以下文章来源于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霍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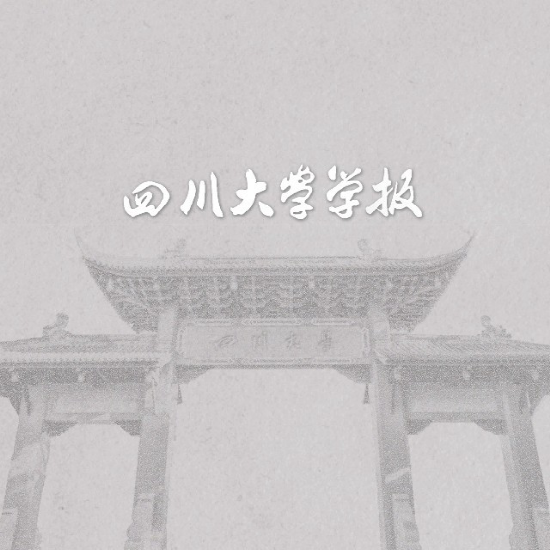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教育部主管、四川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现国内统一刊号为CN51-1099/C。本刊发表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的优秀学术文章,旨在为世界范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个传播与交流学术问题的平台。
作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

大纲
一、三星堆的发现及考古发掘前的准备
二、三星堆早期发掘的方法与具体实践
三、三星堆早期发掘与“古史重建”
四、余论
1928年,继李济先生于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之后,“中研院史语所”又组织了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并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方才终止,前后共计15次。殷墟遗址的发掘,意义十分重大,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它不仅为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确立了一系列技术、方法体系,而且还规定了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可以说中国考古学根植于安阳殷墟的传统。”[1]著名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安阳殷墟发掘对于中国“古史重建运动”的独特价值。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伊始,便选择了以安阳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这与当时传统金石学的发达和“新史学运动”的勃兴均有着密切的联系。殷墟发掘是刚刚成立的“史语所”在傅斯年新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以重建中国古史为目标的一个重大举措,其中固然有早年小屯等地出土甲骨文的因素在内,但事实证明李济领导下的殷墟发掘,早已超越了寻找甲骨文的学术目的,而是十分明确地指出,要以殷墟发掘为契机,重建整个中国文化的体系,“我们相信,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上;要建设一部信史,发展考古学是一种必要的初步工作”。[2]因此学术界对殷墟发掘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早年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所形成的科学、全面、系统地重建中国古史的目标不是将考古学维系在了传统的文献史学和金石学的范围之内,而是从更广义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史学的涵义,从而奠定了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科、学术中的独立地位。”[3]正因为如此,中国考古学界通常也将殷墟发掘作为西方考古学传入之后、独立自主的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之一。
多年之后,中国学者徐坚仍然给予了安阳殷墟发掘以高度评价:“在中国考古学的田野经验和方法的积累上,安阳具有不可辩驳的奠基之功。安阳培育了中国考古学的区域性历史知识,即如何辨认地层、墓葬、建筑等遗迹单位,如何发掘,如何对器物进行描述和分类,如何实现考古学器物组合和文化与上古史重建的结合。”不过,同时他也明确地提出,“安阳并非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全部”,在其所著《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书当中,从第二章开始,便指出了安阳之外还存在着“众流”——即当时中国“多元化的考古学群体”,尤其提及“1986年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唤起对葛维汉和林名均于1934年的汉州发掘的记忆”。[4]
那么,早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这次考古发掘,又是如何作为安阳“殷墟传统”之外在中国西南进行的早期考古学实践,为我们留下来一个珍贵的“西南样本”,从而为后来三星堆一系列举世闻名的重大考古发现埋下了伏笔,预设了古蜀文明探源的重大问题呢?在纪念三星堆科学考古9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三星堆的发现及考古发掘前的准备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在成都以北约40公里,秦灭巴蜀之后此地设蜀郡,汉代分设广汉郡,清代称此地为汉州,1913年改为广汉县。根据多种线索综合分析,我们已经基本考证出三星堆遗址中的月亮湾地点首次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的年代是在1927年。[5]按照当时人记载的说法,这年春天,“一位进步的农民想要安装一架牛力水车,在明代灌渠底下挖到了古地貌的更深层,并发现数件砂岩质地的大石环或石璧,以及石质更坚硬的石凿、斧和矛。它们流散各地,直到被董宜笃先生认识到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6]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的实际执行者为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D. C. Graham),他的《汉州发掘日记》(1934年3月6日—3月20日)是如此记录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前所获得的有关出土文物信息的:
1931年春,在中国四川广汉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V. H. Donnithorne)牧师听闻太平场附近有玉璧和玉刀出土的消息。他随后说服戴谦和(D.S.Dye)教授和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的陶将军与他一道去现场勘察并拍照,晋先生作为摄影师随行。器物发现地点位于一座古老山丘顶部的一条大型灌渠中,该山丘较其周边平原高15至40英尺不等,历经2000年的泥沙(由灌渠从灌县冲刷而来)堆积,逐渐变成了约12英尺高的山丘。
据燕道诚次子所述,他们大约从1927年开始在灌渠底部发现石器,其后每年清理渠底的淤泥时都有发现。这些石器起初被当成无用之物送人。董宜笃先生劝说陶将军购买了4把玉刀和1块玉璧,并将其赠送给华大博物馆。
燕道诚长子告诉董宜笃先生,这些器物都是在一个长方形的坑洞中发现的,其两侧列有石璧,石璧中间有圆孔,这些石璧按尺寸大小排列,最大的直径约为3英尺,总共约有20个。出土这些器物的坑洞在灌渠底部以下约3英尺处。这些石璧下发现了一批令人瞩目的玉刀、众多的玉斧,以及若干包括手镯在内的一些玉环。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石珠。
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葛维汉在日记中记载:“1933年秋,葛维汉致函董宜笃先生,希望获得关于获赠玉器的更多信息。为此,葛维汉逐步制定了一个计划,欲前往广汉发现玉器的地点进行发掘。”目前,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获知葛维汉所制定的发掘计划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但他在日记中却明确地记载,同年的3月1日,他再次前往广汉,“为发掘工作做最后的安排”,并声称“在此之前,其业已获得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四川省教育厅的首肯”。[7]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汉州发掘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获得了“四川省教育厅与四川省政府的批准和发掘执照”;“感谢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和四川防区驻军的官员,他们签发了发掘必要的执照,并给予必要的批准和保护”。[8]这里牵涉到一个十分关键的细节,即在这次发掘工作的准备阶段,葛维汉所称“已获得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四川省教育厅的首肯”甚至获得“发掘执照”是否真实可信?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次考古发掘不仅是西南地区首次科学考古之始,也是首次的“涉外考古”,当时的真实情况又究竟如何?
从宏观的历史背景上看,早在1930年,国民政府便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并于1931年6月15日正式施行。1931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从法律上规定文物属于国有,古物发现者有向地方政府报告的义务,关于地下的古物发掘,则明确规定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之学术机关为之”,并须经过教育、内政两部会同核准后方可获得发掘执照,在发掘时还须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员监管。在《细则》第13条还明确规定:“凡外国人民,无论用何种名义,不得在中国境内采掘古物。”[9]十分显然,这是针对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以各种名义在中国境内恣意盗掘、窃取地上地下文物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也体现了国民对于此种行径深恶痛绝的强烈民族情绪。仅在《细则》正式颁布实行两年之后,葛维汉以外国人的身份,要获得当局——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恐怕都是难以成功的。
透过葛氏日记中闪烁其词的字句,我们似乎也不难揣测到他当时真实的处境。所谓“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发掘执照”,迄今为止在四川大学博物馆所收藏的全部有关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旧档中反复核查,均未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果真有这样一份官方的批文,按照旧档当时的管理水平推测,不应当佚失无存,也不可能在现有的所有资料中不留下任何痕迹。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如同葛氏所言,他获得了有关当局某种程度上的“首肯”——这个用词的弹性十足,既可能是见诸文字的文本,也可能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承诺甚至默许。
从另一位当事人、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助理林名均的表述中,或许可以找到其他的线索。林名均在其《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二十三年(1934年)春,罗县长以好古心切,邀葛氏从速办理。葛以此项发掘,非以现代科学方法,不能辨明其层位而求得其时代之价值。然此事在蜀尚属创举,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乃改用县政府名义,由罗氏出面主办,而以发掘工作归由葛氏负责指导进行。时作者适供职于华西大学博物馆,故得参与其事。”[10]笔者认为,林名均的说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能最相契合,这样一来保证了发掘工作是以中方(广汉县)为主(尽管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进行,而外方(西人葛维汉和华大博物馆)则作为发掘工作的业务指导方,如此才有可能得到当时四川省当局和广汉地方政府的许可以及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至于是否有过“正式批准”的“发掘执照”,以当时四川省与中央政府之间极为松散的行政关系而言,完全有可能“天高皇帝远”,四川方面一旦“首肯”,则不必拘泥于这种“表面文章”,未必一定报请中央相关机构审批。四川大学博物馆陈长虹博士对此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任何相关机构的档案里找到葛维汉所言的这份执照,但可以推定他在这个时期确实得到了四川省当局的支持,甚至获得了有相关人士签字的同意书。”[11]这应当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测。在葛维汉执笔撰写的《汉州发掘简报》中,也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3月1日,笔者前往广汉,与当地官员就发掘事宜做最后的安排。令人吃惊的是,就在当天,已经有一队人开始发掘这个地方了。在罗县长了解到不科学的发掘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后,他下令停止了发掘,并邀请笔者带上发掘工具来督导该项工作。发掘工作由罗县长主持,但发掘方法则由笔者全权决定。”[12]那么,抢先发掘的这队人马是否得到当局的正式批准?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这反映出当时发掘前的乱象,背后的支持者估计正是罗县长本人。后来这种非科学的“发掘”被葛氏及时叫停之后,中外双方才又协商达成了由中方主持发掘(虽然这只是名义上的)外方负责发掘技术指导的最终方案。
综上所述,此次发掘工作前期各项准备当中,在能否获得当局的批准这个最为关键的环节上,中外双方无疑通过大量协商和沟通,最终找到了这样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方式,促成了中国西南首次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局和民情之下,不能不说也体现了当事者的政治智慧和操盘能力。这个环节一旦突破,其后所涉及的人力、财力、安保等安排以及与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的协调工作,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从而为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二、三星堆早期发掘的方法与具体实践
从葛维汉写下的日记和后来所发表的发掘简报来看,三星堆首次现场发掘前后只经历了短短10天左右。1934年3月6日,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至3月14日,溪北探坑和其南北两侧的两个探坑的发掘均告结束,从葛维汉的记载来看,3月14日当天上午,“我们完成了发掘,所有地方都挖至生土层”,然后按照考古规程进行了回填。其后又在发掘地点以西、以北打了探洞。葛维汉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每天发掘推进中的细节,随着发掘的进程绘制了发掘平面图、地层剖面图以及若干器物线图,还将每天的出土器物按顺序编号,并尽可能逐一记录其出土位置。[13]后来,他又根据这些资料完成了《汉州发掘简报》。
对于此次考古发掘的技术方法,1936年正在伦敦留学的夏鼐先生在阅读了葛维汉的《汉州发掘报告》之后,在其3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一大段评论:
至艺术研究所,阅Graham在四川汉州所发掘史前遗址的报告。此君似未曾受过考古学的训练,故报告之缺陷甚多:(1)照片方面,无地层断片、遗物未移动以前位置等的照相,却多发掘者、官吏等的照相;(2)关于地图,无比例尺,地图及遗物图线条皆过于粗;(3)地层剖面图,X剖面图者三幅,而Y剖面者则完全没有,实则就此遗址而言,Y剖面者更为重要;(4)关于遗物的个别叙述,过于琐细,不曾用分类的方法加以系统化;(5)以陶片甚多,遽以为陶窑遗址,似为未妥,因颇多玉器、石器,铜铁器亦有发现,而以为未经人工为言,似属可疑,且谓铁器亦类刀剑碎片,疑为周末之物,铜铁器当已盛行。遗址中罕金属器,亦为铜铁器时代遗址之一般现象,以其不像陶器、石器破碎后即不可用,故居民移迁,都行携去,仅偶然遗失的金属物可以给我们发现,故一个时代(Age)偶用一两件铜器,不能算是铜器时代,但一个遗址中发现一两件铜器,这遗址便可归入铜器时代中去了。此遗址中发现玉器、玉圭、玉琮等物,殊可注意。[14]
如果以后来夏鼐先生作为中国当代考古学奠基者之一的学术地位来讨论和评价葛维汉当年的考古工作,似乎大可“盖棺定论”;但若将其置于西方考古学初传中土的中国早期考古学视野之下,却仍有讨论之余地。夏先生的这一大段评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针对的是考古发掘具体的操作方法;另一部分则是对遗址性质与年代的看法。在第一部分中,夏先生的有些批评是中肯的,他当年只是一位欧陆留学生,就能从葛维汉的发掘简报中发现若干问题,颇具慧眼。例如,葛氏对于所发掘的探沟剖面的记录十分详细,却忽略了平面与剖面的结合;葛氏虽然详细地记录了每件出土器物所属的探方及其在所属探方中的深度,却未记录其在平面上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夏先生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其次,对于遗址的性质推断,夏先生批评葛氏因出土陶片甚多,“遽以为陶窑遗址”似为未妥,也是正确的。不过此处需要略加说明的是,细审葛氏的《汉州发掘简报》,他因探坑中出土有玉刀、玉琮和玉璧,实际上推测其性质“极可能是一座古代墓葬”。至于关于“陶窑遗址”的推定,则是指其对所发掘的三条探沟中所涉地层的推测。葛氏认为:“三条探沟中均有一未经扰乱的地层,那是一个古代陶窑的废弃堆积。该地层最浅处离地面仅一英尺多点,有的地方深达四五英尺。在这一地层中发现了数百件陶器碎片、大量破碎的石器残块以及少量保存完好的器物、三颗珠子和三件小玉。”[15]在这两个方面,葛氏的推测都有问题。因当时发掘的各坑当中从未发现人骨遗存,所以仅仅根据坑中发现有可用于祭祀的玉器,便推测其性质可能为“古代墓葬”显然难以成立,这个情况和1986年三星堆遗址中一号、二号“祭祀坑”发现后的情况极为相似。1986年这两个“祭祀坑”也曾一度被发掘者推测为墓葬,后来才改定为“祭祀坑”(虽然这个定性和定名至今在中国考古学界也仍然存在争议)。而葛氏所推测的“陶窑遗址”,后人经过再次调查,认为应为遗址中的“红烧土堆积”,其性质可能为“房屋建筑坍毁之遗迹”,[16]显然更为合理。
对于葛氏在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的具体操作层面,用今天考古学的眼光来看,除了夏先生所批评指出的缺陷之外,后人还指出他“对文化层的划分太过粗糙。因为缺乏对土质、土色的细致观察,没有划分出更细的层次,所划定的文化层厚达一米左右”。[17]
应当承认,上述这些批评意见,都是成立的。但同时也应当指出,这正是当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早期考古学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关于地层学的实践过程中,葛维汉对“文化层”的划分,很显然也受到地质学的强烈影响,还没有将自然的地层堆积和人类活动形成的“文化层”堆积很好地加以区分,才会出现“所划定的文化层厚达一米左右”的现象。这和中原殷墟发掘初期发掘者也因为认识上的局限性而采用所谓“水淹说”解释各种地层现象,将殷墟文化层看作是“数次大水淤积而成”,从而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进行了错误的解释,[18]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之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必苛责前人。如同陈星灿先生在回顾中国早期考古学实践中关于地层学原理的运用时曾经总结的那样:“按人为的水平层发掘方法曾是上个世纪及本世纪初十分流行的方式,安特生采用了这种方法,李济早年的发掘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安特生本身是地质学家,采用这种方法自不足怪。李济本身是人类学家,他在美国留学时代,美国考古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水平层位的发掘方法。”[19]随着中国早期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才逐渐开始在地层学上学会以文化层、而不是以人为的水平层划分地层以及对遗迹打破叠压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从总体的技术操作层面论,葛维汉所采用的田野考古方法,和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考古学方法是基本一致的。根据他的发掘日记和发掘简报,其基本的工作流程是:首先,采用“探方法”和“探沟法”在发掘区域地面布方,“我们首先在要发掘的地面用标桩划出一些五英尺见方的探方。每根标桩上都有一个编号,每个探方的编号即其右下角标桩的编号”,“我们首先在零基准线与五英尺线之间挖了一条长40英尺、宽5英尺的探沟,探沟深至碎陶器出土地层或其他有人类活动痕迹的地层以下几英尺”。其次,逐层向下发掘,同时做好发掘记录与工作日记,“出土的每件器物都要编号,并登记在田野记录本上。我们在记录本中仔细地记录了每件器物的出土深度和平面坐标及其他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还绘制了平面图和地图各一幅,并留有完整的工作记录”。最后,当发掘至生土层时,发掘工作结束,并对发掘坑进行回填,“发掘结束后,所有的沙土都被回填到沟里,地面也被仔细平整。农民因允许发掘和庄稼受损而获得了补偿”。[20]
上述方法和今天田野考古的基本流程并无太大差别。所以,夏鼐先生批评葛维汉“此君似未曾受过考古学的训练”之说,可能难以成立。已经有学者研究指出,葛氏虽然主攻文化人类学,但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曾在导师柯尔指导下学习考古发掘的理论与方法,并参加了“南伊利诺伊州印第安土丘的发掘”,[21]他在月亮湾发掘时所采用的“5英尺方格法”,是美国考古协会所推荐的方法,这也是当时英美考古学界通用的探方法。从这些线索均可推知,葛氏应是受过一定程度考古学训练的,他在月亮湾的考古发掘,正是他从美国带来的西方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西南的首次实践。
还值得注意的是,葛维汉在这次考古工作中,还十分重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结合,他请华西协合大学化学家柯利尔(H. B. Collier)博士对发掘出土的陶片样本作了化学成分的分析,请华西加拿大学校校长黄思礼(L. C. Walmsley)对出土玉器和陶器的色度等也作了分析,其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自然科学的观察与分析掌握更多的出土材料信息,尽管这些工作还非常初步,但无疑已经开启了今天已经成为考古学界基本方法的“科技考古”之先端。
此外,在出土文物的处置上,葛维汉首先将其全部带回到广汉县城,并交给县长罗雨苍,表示对名义上的“发掘主持者”、也是中方权益代表者的尊重,然后由罗雨苍在1934年3月19日于广汉县政府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捐赠仪式,罗雨苍、葛维汉以及广汉众多官员、民众齐聚现场,在参观了这批发掘出土器物之后,由罗雨苍宣布将其全部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并希望华大博物馆能够“为华西民众永久保存这些器物”,而葛氏随后也当众表示“郑重承诺这批文物将永远珍藏在华大博物馆”。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作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时任馆长,葛维汉也认识到利用此次发掘出土文物开展民众宣传的重要性。根据多方线索综合分析,此次出土文物首先是在广汉公园内设立的文物陈列室进行过短暂的公开展出,[22]当这批文物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之后,葛维汉、林名均等首先对其进行了建档登录,所列项目包括文物的总登记号、藏品号、名称、地点、来源、征集者、入藏时间、征集时间等各项细目。这批宝贵的文物档案资料一直妥善地保存至今,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三星堆早期发掘出土文物不可或缺的史料。其后,华大博物馆就此辟出专柜对外公开长期展出这批出土文物,据研究者描述:“展览安排在懋德堂二楼北翼。展柜为玻璃橱窗式大通柜,……第一层以玉器为主,包括两件经过修复而相对完整的陶器,第二层为陶片,第三层为各种石器。柜外开放式陈列三件玉璧,斜靠展柜,从大到小排列。”[23]从华大博物馆公布的资料照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展出专柜的情况。[2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评价由葛维汉实际主持的三星堆首次科学发掘的价值和意义,他所采取的田野发掘、记录的方法虽然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但总体而言是符合由欧美传入中国的田野考古规范的。他在研究方法上引入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这对于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研究范式无疑是新的突破。对于出土文物的归属问题,他能够尊重中方权益,采取协商的方式达成最终的保存方案,使得这批早期三星堆出土文物能够永久性地保存于中国,避免了这个时期大量中国文物因为国外所谓“考古”“探险”活动而大量流散于海外的情况发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华大博物馆馆长的身份,充分关注到出土文物展示、宣传的重要性,从广汉发掘现场到华大博物馆,都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开出土文物信息,这对于增强民众对于本土文化的重视和关注、缓释民众对于外人参与中土发掘的疑虑与紧张情绪,应当说都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三、三星堆早期发掘与“古史重建”
从宏观历史背景上观察,早期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所形成的“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其核心价值既包含了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内容,更设定了更为深层次的思想方法和目标追求。简而言之,殷墟传统是中国当时“新史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新史料的扩充为基础,强调科学的方法和多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古史重建”为最终目标,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早期考古学范式。如同李济先生早年在对殷墟发掘的学术目标进行设定时所明确指出的,要以殷墟发掘为契机,重新构建整个中国文化的体系。[25]
那么,我们又应当以何种眼光来看待三星堆早期发掘与殷墟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来评价三星堆早期发掘与“古史重建”之间的贡献呢?
有资料显示,葛维汉对于早在1928年就已经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是有所关注的。在他撰写的《汉州发掘简报》当中,就将三星堆月亮湾地点出土的石器、玉器、陶器与安特生在仰韶和沙锅屯的发掘,以及李济在安阳的发掘作了对比。他甚至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有的与《安阳殷墟简报》第一部分所披露的一件三足陶器“有着一模一样的饰纹,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博士认为是仿丝带或丝绳纹。李济博士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安阳文化和广汉文化中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纹饰,而安阳文化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122年的殷商时期”。[26]他还在发掘工作结束不久,便主动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徐韦曼博士,寻求与中央研究院之间的合作。在信中他写道:“我知道中央研究院做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工作。我在哈佛大学听说了很多关于李济博士的事。最近,受广汉县县长的委托,我和馆长助理林名均先生在广汉附近发掘了一个遗址。我们获得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和石器,这些陶器的时代可以追溯到汉以前,最晚也可以追溯到周代。”[27]
葛维汉本人对于广汉月亮湾地点出土器物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材料背后所涉及的文化背景,不是没有思考的。他在《汉州发掘报告》中提出了他的认识:
这些器物清楚地反映了广汉文化与中原和华北地区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交流与传播——要么当时居住在广汉地区的是非华夏族群,但其文化受到了中原和华北地区早期文化的极大影响;要么是华夏人及其文化进入四川地区的时间比人们认为的要早得多。……我们认为,广汉文化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周朝初期,或者说公元前1100年左右,但进一步的证据可能会使我们将其年代推至更早时期——其年代上限应为铜石并用时代。[28]
即使从今天三星堆考古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料来看,葛维汉根据当时仅有的出土器物所得出的这些认识,虽然不甚精准,应当说也是大体上可靠的,今天对于“三星堆文化”,亦即葛氏所称的“广汉文化”的考古学年代的推定,也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最盛期为商代晚期,下限到西周初年。[29]因为葛维汉毕竟对于巴蜀古史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所以对于此次发掘所涉及的古蜀文明,他没有提出更多的见解。不过,他能够清楚地指出“广汉文化”与中原和华北地区早期文化之间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已属难能可贵。
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三星堆早期发掘所引发的思考和讨论,已经深入到重建古蜀历史的更深层次,与中原殷墟发掘所带来的对于晚商史迹的追溯,经历了相同的学术轨迹。
最早将三星堆月亮湾考古发掘和古蜀历史联系起来的,首推当时还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先生。在考古发掘之后不久,郭氏就获悉了这个消息,并向发掘者之一、华大博物馆馆长助理林名均寻求相关资料。在获得并阅读了这些资料之后,郭氏于1934年7月9日给林名均回信,信中除高度评价此次工作“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之外,还对遗址的年代、性质,尤其是与文献记载中“蜀”的关系提出了看法:
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中原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中原、华北有过文化的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广汉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广汉遗址的年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30]
以往对于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蜀”的具体地望,学术界颇存歧义。正是由于三星堆此次考古发掘,才使得郭沫若先生有把握将其与“古代西蜀”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参与此次发掘工作的林名均先生在当时所发表的意见给予高度的重视,既往研究史中很少关注到这位华人馆长助理的研究成果。
继《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之后,林名均应《说文月刊》编者卫聚贤之请,于《说文月刊》在重庆出版的《巴蜀文化专号》上,发表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他在文中评价由葛维汉执笔撰写的《汉州发掘简报》称:“其中虽颇有可商榷之处,然大体尚称完备,……乃根据平时参加发掘经验及个人研究所得,并参考葛氏报告,草成此篇。”这篇文章分为绪言、遗物之发现与保存、发掘经过、各遗物研究、时代之推测、广汉遗物出土之重要等6个小节,对此次发掘工作进行了总体性论述。其中最具价值之处,首先是林名均首次在“时代之推测”一节中,将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分为两个时代:一是溪底岸坑中所得之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殷周之前也”;二是溪底墓中之物(林名均此时仍将器物坑认为是墓葬,乃误)“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这在葛维汉对遗址年代的总体认识上,更加细化了一步。
其次在“广汉遗物出土之重要”一节中,他更为深入地论述了广汉发掘收获与古蜀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古代之蜀,向皆目为戎狄之域,必无文化可言(《国策》记司马错伐蜀事,张仪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今观广汉出土诸器物,其制作之精工,实无逊于中土,若加玉器之使用,尤足显示其文化之崇尚复杂。由此可改变吾人对于古代四川文化之基本观念。
(二)由前所述,可知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关相似之处,则古代蜀中文化所受中原文化之影响,实不难窥见其痕迹。盖四川与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谓:“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史记·五帝本纪》亦谓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其说虽未可尽信,然蜀之名早见于殷代卜辞,武王伐纣,蜀人预焉(见《尚书·牧誓》)。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之文化,亦无不可。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实甚有贡献也。[31]
林名均对于中国古史文献的熟悉程度显然远在葛维汉之上,所以他的学术眼光显然也相较葛维汉更加深远广阔。在当时仅有的考古资料可供利用的条件之下,他首先从玉器制作和使用的观察视野切进,认为四川古代文化实际上已经具有“崇尚复杂”的特点且“无逊于中土”,因此国人应当改变视古代四川文化为“西僻之国”的陈旧观念,这一判断和后来三星堆考古重大发现所显示出的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达程度是完全吻合的。其次,在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上,他以独到的敏锐目光,根据考古发现和古史记载,认识到四川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起甚早,甚至提出“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之文化”的观点,虽显粗糙不精,但亦不乏其中的合理因素,这就是从中观察到古蜀与中原文明之间的联系与统一性。更为难得的是,林名均从广汉出土遗物还思考到更为广阔的“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这就从区域性的历史知识,扩展到对于中国文化总体性的认知,对于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轻视中原以外周边区域史地研究的倾向,鲜明地表达了他从全局上强调中华文化具有统一性特征,需要从一时、一地之文化出发,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考察其在中国古代总体文化分布上的意义与价值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文化观念也绝非单纯的“地域文化论”,格局甚为广大。
四、余论
综上所论,如果说安阳殷墟发掘所形成的“殷墟传统”确立了在早期中国考古学建立过程中的地位;那么三星堆的早期发现和发掘也是不应当被埋没的一段历史,它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观察、认识和理解中国考古学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区域去考察20世纪30、40年代随着古老的中国进入一个大变动、大变革、大变化的时代之后,在新文化运动所导入的“民主与科学”潮流的激荡之下,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的中国北方和南方是如何以“重建古史”为目标,各自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概括而言,三星堆早期发掘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历史背景之下,中国西南首次进行的科学考古尝试,它不仅与当时中原、北方地区的早期考古发掘工作遥相呼应,同时也在“重建国史”的总体目标之下,为区域性的古蜀文明探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考古实物证据,对于正确理解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之间的关系,也首次提出了客观的判断。在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从考古发掘工作的前期准备,到正式开展发掘工作,直到后期的资料整理与阐释,甚至包括对公众的科学宣传普及,三星堆早期发掘都给我们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和实践经验。直至今日,国家文物局倡导“大考古”,回顾早年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似乎都在与之遥相呼应。
毫无疑问,安阳殷墟发掘在当年所取得的成绩、产生的学术影响以及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都要远超同时代的三星堆早期发掘。但如同浩瀚的大海都是由一朵朵浪花组成一样,在历史的潮流当中,正是像早年三星堆考古发掘这样的涓涓溪流,最终汇入中国早期考古学的科学实践之中,才最终形成了今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横跨江海、走向世界的滚滚洪流。
注释
[1]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2]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3]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与研究》,《古代文明》第4卷,第382页。
[4]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396页。
[5]霍巍、谌海霞:《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新考》,《四川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
[6]戴谦和(D. S. Dye):《四川古代的圆形和方形土石遗存》,原文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4卷,1931年(“Some Ancient Circles,Squares,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zechwan,China,” Journal of West China in Research Society,vol.4,1930-1931,pp.97-105),此处译文采自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95页。
[7]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1934年3月6日—3月20日),蒋庆华译、代丽鹃校,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211-213、215页。
[8]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蒋庆华译、代丽鹃校,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339、363页。以下凡有关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译文均采自此文,下不赘引。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09-611页。
[10]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410-411页。
[11]陈长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与三星堆早期发现》,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24页。
[12]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第339页。
[13]陈长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与三星堆早期发现》,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30页。
[14]《夏鼐日记》卷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8页。
[15]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第347、346页。
[16]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322页。
[17]王波:《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1934年广汉太平场月亮湾发掘所获陶器概况》,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129页。
[18]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古代文明》第4卷,第358页。
[19]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37-238页。
[20]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第345-346页。
[21]付云:《民国学术视野下华大博物馆的考古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第159-160页。
[22]陈长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与三星堆早期发现》,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30-32页。另月亮湾燕家后人燕仁安在1951年向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文物时透露,1934年考古发掘后,出土器物曾在广汉公园内陈列室展出,参见邓穆卿:《房湖公园今昔》,政协广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5年,第82页。
[23]陈长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与三星堆早期发现》,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43页。
[24]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365页照片,题为“华大博物馆广汉文物展柜”。
[25]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第2页。
[26]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第360-361页。
[27]葛维汉致徐韦曼的信,1934年4月11日,原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档案号2010-253。又可参见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393-394页。
[28]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第361页。
[29]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1-170页;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30]此信原件现已不存于四川大学博物馆旧档,但在葛维汉《汉州发掘简报》中有全文引用,此处译文参见甘霖、霍巍主编:《三星堆考古九十年·三星堆早期考古发现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第362-363页。
[31]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巴蜀文化专号》),第93-101页。
编辑:吴 茜
审核:邱 爽
终审:周维东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内容来源: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